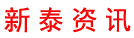结怨于项氏家族
我叫李成才(苗名:甘巴•李),苗族,生于1927年8月1日,云南麻栗坡县猛硐乡东瓜坪自然村人。
我祖辈清朝末年,从西畴县马街地区迁入猛硐地区的香草棚自然村。我十二岁进入猛硐项氏家族创办的私立学校读书。学校校址位于当今的猛硐中学右侧的赵家处。校长是项朝凤,教师有罗金希、罗林恩等。小学学制六年。
我读完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国民党麻栗坡对讯特别区督办公署在猛硐开办了一个师资干部培训班,学制一年。该训练班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干部和师资队伍。我入选进训练班继续深造,同班同学中,我记得的人有陆登文、梅家仁、朱桂芬(女)、陆仕芳(女)、陆玉升、陆胜贵、王延珍(女)、李成怀、王兴安、罗成恩、李友义共有11人。校长是廖继林。训练班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历史和电服秘码等,全班同学均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员。
训练班毕业后,全班同学中,大部分在当地新设的小学样任教师。我分配在猛硐(天保讯)讯公署负责猛硐区域内的户口清理工作。猛硐地区的户口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年。工作结束后,我又调到麻栗坡的茨竹坝开展同样的工作。我在茨竹坝干了两个月,工作结束后回到猛硐。
1940年秋,我听说马关中学招生,就随即到马关报名。我急匆匆赶到马关县城时,因迟到了一天,学生已招满,学校拒收。于是,我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走到都竜时,遇上了曾在猛硐担任过汛长的杨兴国。
“李成才,你不要回去了,我们准备在沙仁寨办一所民办学校,正缺老师,你去那里教书吧!”杨兴国安排给我的这个差事,很乐意,就接受了下来。
我没有回家,直奔沙仁寨教书。那时的民办学校没有工资,粮油等生活物资,由当地群众捐献。我在沙仁寨工作一年后,又调到田坝心小学任教,在田坝心教了一年的书。
1943年8月,我又获悉麻栗坡中学招生,辞去了小学教师工作,前往麻栗坡中学就读。当时,麻栗坡中学旧址位于当今的电影院。校长是唐兴贤,教导主任是梁惠。全校师生六百余人,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学制三年。我如今记得的同学有来自八布的关顺祥、罗成仙。我们三人考试成绩每次都名列前茅。我在麻栗坡读书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已在麻栗坡开展活动,其活动中心就在学校里,我们大多数学生时常参加共产党的秘密会议。当时,为了掩人耳目,我们都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活动。从那时起,我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政策教育。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有类似的活动,我都参加,决心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1945年秋,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麻栗街的上空,中共地下党人廖万里、柴贵学和一位姓朱的同志被国民党麻栗坡对汛督办谢崇琦派人暗杀在麻栗坡街。一时间,麻栗坡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学校陷入一片混乱,学生走的走,逃的逃。
我没有完成学业,跟随一部分同学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我到越南官坝学习,我和王忠顺同学经过几天的长途拨涉,进入了官坝。
我们在官坝,见到了我们的老师,麻栗坡中学的教导主任梁惠。他给予了许多鼓励。
我们在官坝学习的有100多人,学习期间,从国内传来消息,猛硐的项朝宗也参加了革命。不久,项部的项朝顺、项朝志、项朝安、王国忠也来到了官坝参加学习。
项朝宗部背叛革命后,在官坝学习的项部几名骨干离开官坝返回猛硐。我仍坚持在官坝学习,还认识了一位姓赵的铁厂汉族人,这位姓赵的汉族人学习期满后,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回国进入猛硐地区开展地下斗争工作。由于工作不慎,身份暴露,被项部的项廷长在现今野猪塘与昆脑盆路附近的山沟里杀害。
1945年冬,我离开官坝回国,返回到猛硐探家。人一到家,就听到一些传闻,项朝宗要对我家下手,斩草除根。一家人沉浸在恐怖的气氛里,大家都很害怕,预感到一场灾害即将来临。
项部为什么要对我家下手,事情得从苗瑶械斗事件说起。那是1938年的事了,项家发动武装对瑶族进行攻打,激起瑶族公愤,瑶民联络其他民族反抗项家,瑶民攻入猛硐,掘开了项崇周的坟墓,将其尸骨焚烧后,装在火药枪内射向天空。项崇周的墓按苗族习俗,葬有两合棺材,内为棺外为套,均属猛硐地区出产的珍贵秃杉。瑶族人掘出棺材内的尸骨火烧后,棺材依旧裸露在外,项家因战败撤离猛硐,逃往他乡。我父亲和我的叔叔看到裸露的棺材无人照管,就把项崇周坟墓里的管材盗出,卖给了马关县的木材老板。棺材运到了马关县城内。一天,项朝宗的大哥项朝宝狂街时。在兴隆看到有人正在加工这盒棺材,项朝宝心生疑问,顺便向加工棺材的人打听棺材的来历。
“你们有好棺材嘛?像这样好的秃杉棺材现在可是很难找到了,你们在哪里买的呀?”项朝宝问。
“是猛硐香草棚李小二和李小三两哥弟运来卖给我们的。”这家做棺材加工的主人回答说。
项朝宝听了主人的回答后,事情已经明白了一大半,他突然想到:“我爷爷的坟墓被瑶人挖开后,棺材还在。可是没过几天,棺材就不见了。”项朝宝想到这里,就对棺材进行仔细检查,发现有烧过的痕迹。原来,这棺材里真是他爷爷项崇周墓内的棺材,真相大白。
从此,项家埋下了对我家的仇恨。
那年的大年三十这天,我大爹家杀年猪,族内人沉浸在欢乐中,唯有我和父亲李正福(外号李小二)、叔叔李正元(外号李小三)十分焦急,原因是我杀了一只鸡祭献项崇周,鸡卦显示出的信号是“无口有脚”,意思是“快走”。时间到了中午,忽然从下阳坡方向传来枪声,按贯例来讲,这是项家有事出山。
“不好了,项家打来了。”我迅速跑到家门前的小山堡堡往下一看,只见项朝宗带着大队人马朝我家奔来,因为我家住在高处,看得十分清楚。
“可怕的事情来到了,赶紧逃跑!”我的父亲朝我叔叔大喊一声,丢下家里的东西,拖着老婆孩子就逃跑。
我们朝野猪塘方向逃去,跑出三百多米的地方,我们刚钻进草丛,就听到一阵枪声在我家响成一片。项部扑空,幸好他们不知道我家逃跑的方向,不然,只要几分钟我们就会被抓住,真是老天保佑啊!大家吓得直冒冷汗。
我们在草丛里躲藏起来,不敢露面。项部在我家折腾了一阵子,就走了。我们一家顺着小路来到野猪塘水沟头的深山老林里暂避,接着往森林深处去。一星期以后,我们逃入越南黄树皮地区的甜竹坪自然村落脚。
甜竹坪是黄树皮地区的一个偏远苗族村寨,因为这里有我家的亲戚,我们一家才得以暂时居住下来。但是,若要长期居住下去,十分困难,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法国官员是不允许的。这里的亲戚向我们提出解决办法,买通州官。我一家为了得到期长居住,父亲叫我把家里的一只大白狗拉去送给了黄树皮的王州官,王州官又把大白狗送给了法军三圈官。就这样,我们家得到法国人的允许,同意长期居住下去。
我当上了法国兵
我家在甜竹坪居住下来后,过上了安全的生活。用不着担心项部前来报复。
很快,法军驻守黑硐的大队长李小左(当地苗族人)来到甜竹坪,他找到家里来,他根本就不商量,发给了我一支枪,一套衣服。我从此参加了法国殖民军,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法国兵。李小左叫我随他上黑硐守阵地。
黑硐,位于越南北部边境清水河上游的老寨自然村与东瓜林自然村之间的大山顶上,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法军在这里没碉堡,主要防范中国军队的进入和周边武装势力的入侵。
驻守黑硐的法军有四个大队,400余人,军官是法国人,士兵是当地的苗、壮、傣、瑶等少数民族青年。我驻守黑硐的那些日子,项朝宗带兵来攻过,但没有得手。
1947年2月初,黄树皮的王州官来到黑硐巡视。他见到我,显得格外关心。
“李成才,我告诉你一件事,项朝宗到现在都不放过你,他抓了16个越南人民军交到黄树皮洋人三圈官那里,说要拿这些人交换你。洋人没有答应,只给项朝宗十二驮子弹了结这件事。”王州官说。
听了王州官的话,我半信半疑。我想,是项家让我一家背境离乡,客居异国,有家不能回,这一仇恨难以从我的心中抹去。当时,我也明白,法军故意抓住我与项家的仇恨,编造事实欺骗我,让我更加死心踏地孝忠法军。
时隔不久,项朝宗来到了黑硐。法军一圈官热情地接待了他,项朝宗与法军一圈官交谈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但不难看出,项朝宗是与法军达成了某种协议。事后,项朝宗就把他的堂妹嫁给了法军总甲千章•杨(又称杨千章,现今越南河江省辖地的普捧苗族人。越南独立后,法国殖民军撤出越南,千章•杨随同移居法国。)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担心起来,害怕在法军里呆不下去,我提心吊胆度日。那年的秋季来临,我被调离黑硐,来到黄树皮法军情报处工作,原因是我懂法语、壮语、汉语、越语,又是本地方的苗族,对法军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因此,我不但消除了在法军呆不下去的疑虑,相反还得到法军的重用。我的一切思想顾虑打消了,专心地为法军工作。
我离开猛硐,逃入越南以前,就结了婚,妻是上阳坡项朝义的妹妹,名叫项朝妹。我们生有一个女儿,叫咪杨。我是独儿子,我叔叔也只生有一个女儿,所以,我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虽然,甜竹坪自然村地处黑硐与黄树皮之间,相隔只不过半天的路,但我很少有探亲的机会,法军的军规较严。尽管这样,在法军军营里自己过得挺好,家里的人自然也就放心了,我也很安心,只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苦了我的妻子,总觉得对不起她。

奠边府的法国空降兵
1948年春,法军派我前往猛硐,与项朝宗会面。我为了安全起见,带着熊小老(现居住在猛硐哪秧村)一同进入猛硐。我们的任务是缓和我与项的矛盾隔阂。刚开始,我接受任务后,感觉到不安,担心遭来不测。不管怎么样,是洋人派的差,硬着头皮去与项朝宗见面。那次,我和熊小老走了一天的路,来到猛硐。项朝宗在他的总部驻地(现今猛硐粮管所右侧)迎候我的到来。项朝宗身材高大,满面笑容,十分客气,问寒问暖,他的言行举止消除了我的思想顾虑,感觉不到有什么危险,何况我与项朝宗还是老表弟兄。
这次会面,我与项朝宗只谈了些当前的形势,外加一些无关紧要话题,全是谈天说地,对两家之间的旧仇只字未提。那天,项朝宗热情地招待我的吃住。次日,我就与随从熊小老返回黄树皮了。
从猛硐回到黄树皮不久,我就被法军派到风丫口法军驻地工作。风丫口位于中越国境线三段十号界碑附近,那里是中越两国官民往来的主要通道。那时,两国过往人员繁杂,而我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情报搜集工作,主要搜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和马关县杨国华匪部的情报。我经常站在风丫口驻地朝北望,都竜、猛硐两地的大半区域尽收眼底,各条通道历历在目。这些对我的工作很有利。当然,更多的是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
我在风丫口驻了三个月,因患上了重病,得到法军官的批准,回到甜竹坪家里休养治疗,在家住了四十多天。病好转,我又接到命令返回黄树皮法军营地。
亲历奠边府战役
我一回到黄树皮,就随法军往越南内地行军。当时,我的病还没有全愈,就骑着马行军。我们撤离黄树皮时,行动紧急,没有让家人知道,这一去,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人也不知道我的下落。
我们大队人马从黄树皮出发,途经箐门、天也、白河、漂龙(文献上称“发隆”“花龙”“龙坪”)勐康等地。一同行军的还有法军的苗族军官千章•杨、王州官等人。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行军到达了老街。法军河内总督府传来命令,部队就地在老街待命体整。我们一呆就是九天的时间。这期间,千章•杨、王州官因是法军要员,乘飞机飞往河内去了。
法国发起的殖民战争已经打响,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军队在越南北方广大地区向法国殖民军展开全线进攻。法军在局部地区失利,局势十分混乱,我无心随法军行动,就开小差,带着两个随从私自离开部队逃跑。
我们三个人逃到了一个叫勐圭的地方,由于人地生疏,又身无分文,活命要紧,只好滞留在勐圭,靠帮人家打工度日。这期间,不断听到法军在战场上失利和逃跑的种种传闻。为了搞清真实情况,我们就跑到法军的驻地——沙巴(又称沙坝)看究竟,到了沙巴一看。果然,到处都是被烧焦和丢弃了的汽车、飞机等。法军早已不知去向,逃难的人络绎不绝,我们融入到逃难的人流中,逃往内地。
我经过一段艰难行程后,逃到了莱州的勐录,我在勐录,看到法军正在加紧建设飞机场,我没有归队的意思,又继续向前逃。1949年初,我来到一个叫勐梭的苗族村寨,因为语言相通,我就在这个村寨住了下来,我就为了安身,不再过流离生活,我认识了苗女王咪珠,并娶了王咪珠为妻。当然,我是以上门的身份娶她的。咪珠有一个哥哥,叫王咪达。我与咪达时常在外跑生意,为的是把家庭生活改善好。我在咪珠家落脚以后,每逢勐梭街,我与咪达杀猪、杀牛卖赚钱来糊口,因生意上的奔波,回到咪珠的身边很少,虽是夫妻,却过着牛郎织女一样的生活。我和咪珠生活一年时间,没有生育孩子。
1951年3月法军开到勐梭来,在勐梭修起了飞机场,法军中有人是我的熟人,他们见到我在勐梭,就把情况上报给法军高层指挥官。法军高层下了命令,派兵到处搜捕我。一天,我和咪达驮三驮花生去勐梭街卖。那正是街天,我在街上被法军抓获。法军将我的花生撤在地上,强迫我赶着三匹马跟法军走,但是他们释放了王咪达,临走时,我对咪达说,叫他回去后转告咪珠。我会回去找她。我想,这次肯定完了,我是个逃兵,不枪毙也得脱层皮。管他妈的,人现捏在人家手里,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离开了年轻漂亮的妻子,离开了那个在异国给我温暖的小家庭重回法军那里。我没有受到处罚,而是被调到莱州去,安排在千章•杨身边工作,因千章•杨不识字,我主要负责他的文书和翻译之类的工作。
我在莱州法军军营工作了一些日子后,征得千章•杨允许,我回到勐梭看望了我的妻子咪珠。后来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国的解放军已经从金坪方向打过来,越南人民军从东面打过来,驻勐梭的法军命令我带着一个连撤往莱州,我接到命令,不得不出发,谁知这一去,却永远告别了我那年轻漂亮的妻子,并且直到今天也不知她的音讯了。
在撤往莱州中,情况十分紧急,遭到越南人民军的围追堵截。我们一边行军一边还要抵抗,停下来就要赶快挖掩体。
一天,我们在行军途中停下来休息,法军官立即命令挖掩体,正值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我刚放下工具拿起烟筒抽烟,一法军官就指着我骂,叫我赶快挖战壕,我与那位法军官顶了几句,那法军官就托起一根竹杆朝我打了过来,正好打在我左脚的筋骨部位。我的脚当即骨折,脚后跟筋已露出在外。我把这件事告到三圈官处,很快法军就用飞机送我到河内法军医院治疗。我在河内法军陆军第一医院治伤,在河内法军医院整整住了九个月。医院的医生全都是法国人,法国医生采用的治疗方法是用十多斤重的称砣把我的脚吊起,然后打上夹板,然后就是不停地敷药、吃药。四十五天以后,医生才将称砣拿开,但我仍然不能下地行走,一直躺在床上。法军四圈官院长派了一位法国女护士照料我,由于我行动不方便,除了医生、护士换药以外,我一直是自己一人呆着。几个月以后,我能柱拐仗下地走动了,医院就安排我去海防疗养,因为海防在海边,空气新鲜、环境宜人。我是坐火车去海防的,海防的法军疗养所建在图山岛上。
图山法军疗养所里,有大批法军军官在那里疗养。另外,还有部分当地人。疗养的人中,我还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海南岛的黎族同胞,姓王,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他也是在法军中受伤的。这位王姓黎族同胞受的是枪伤,胸堂被捷克式枪弹击中,住进了法军医院,尔后安排到疗养所疗养。
我在图山疗养所疗养了三个月,直到我的伤全愈,不需要拐杖了。我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恢复,法军军官就通知我返回河内。我离开海防时,那位姓王的黎族同胞还在疗养所里。他的伤没有完全好。法军军官见到我时,问我愿意到哪里工作。我向法军官提出要求,回勐梭去。
“那里正在打仗,你的任务不是去打仗”。法军官说。
“我去哪里,做什么?”我说。
“你还是回莱州去,到情报局工作。”法军官说。
我在河内没住几天,莱州方面就派人来接我。我到了莱州,进入法军情报局工作。法军情报局里人很多,有美国人、英国人等,人员分为若干个组开展工作。我在的那个组,组长是一位美国人,他的名字我忘了,职务是二圈官。因为是做情报工作,各组与各组之间的人员相互不往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做些杂事,帮助那位美国人工作。有一天,那位美国组长向我透露。他说:“兄弟,大战就要爆发了,战场会在奠边府。”
1953年大年除夕,这一天,法越两军宣布停战,双方过年。然而,法军没有遵守协议,突然向越南人民军、中国援越抗法部队发起进功,进行反扑。越南人民军、身着越南人民军军服的中国援越抗法部队,加大了围歼法军的速度,战斗十分激烈。不久,我们就随总指挥部撤往奠边府。我们开到奠边府时,遇到一派忙碌紧张的景象。法军各部队忙着备战,修的修工事,抗战壕的挖战壕,飞机场上更是忙着修筑跑道。
我所在的法军情报局设在总指挥部,也是总指挥部的中心。奠边府地势平坦,有飞机场、地下室、地下通道。总指挥部的地上地下通讯线四通八达,白天黑夜传来指挥官的叫嚷声,局势严竣,混乱不堪。
奠边府战役终于爆发。1954年1月,中国援越抗法部队、越南人民军从四面八方将奠边府完全包围起来,不管白天黑夜,对法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从前线不断传来法军枪炮声,和法军飞机的轰炸声,总指挥部里不停收到法军在前线战败的消息。因为,我们在总部,除了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以外,看不到战斗的场面。但是,设在总指挥部附近的法军战地医院,地势低凹,源源不断有大批的伤员运来,没有几天的时间,医院人满为患,一些重伤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死了许多。我执行任务路过医院,探头望去,尸体堆满了凹地,有几处的尸体还高出医院的房顶。
危急关头,法军总指挥部传来命令,让我指挥一个营,负责保障总指挥部的后勤保障和通讯的联络畅通。我带的这个营是法军从老挝征招进入越南的苗族兵(当地人称黑旗军)。由于清一色的苗族,语言上彼此没有障碍,他们还算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能完成任务。
1954年4月5日这一天,是我最难忘的日子,爆炸声中,总部的人员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有的各自逃命。枪炮声越来越近,十分猛烈,战斗持续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从总部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白旗。几分钟后,我们都被俘了。越南人民军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我们不时看到从各个地方押来的俘虏。我估计了一下,被俘的法军有七八千人。奠边府战役,法国殖民军战败,结束了在越南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我同被俘的人一道,在越南人民军的押送下,朝安沛(又称安拜)方向出发。俘虏中,有一大批法国本土来的法军军官,一路上,人民军强令白天不得生火,只准夜间生火煮饭,目的是防止法国的飞机轰炸。然而,那些法军军官都有意在天亮后生火煮饭,故意将目标暴露给法军飞机,结果目标暴露,引来了法军飞机的轰炸,由于人多不容易疏散,包括人民军在内,每次都炸死不少人,惨不忍睹。类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次。

奠边府战役中被俘的法军
5月10日,我们到达了安沛。我们在安沛期间,越南人民军把我们分批进行政治学习教育,愿意参加人民军的参加人民军,不愿参加人民军的,人民军发给路费回家。俘虏中,有很多是中国人,但大多互相不认识,从口音上辨别,许多是中越边境上的苗、瑶等少数民族。我们在的那个队有46人,有几人还是猛硐响水、坝子的瑶族人,那时,我们不敢相认,只是回国途中才认识的。有几个苗族人是猛硐相邻的越南老寨人,一个是中国猛硐地区的上扣林人。凡是中国人都希望回家。几个月以后,我们终于被释放回家了。我们46人于同年的九月从安沛出发,步行到了河江(河阳)人民军接待站报到。
我途经清水河、老寨进入祖国国境猛硐老家。回到家后,我父亲才向我讲述在越南生活时的情况。我离开甜竹坪随法军走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我的前妻项朝妹已改嫁他人,我的女儿咪杨病故,母亲被土匪杀害,我痛不欲生。我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生活在异国他乡,直到最终回国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十二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我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我父亲及我的叔叔一家又迁回国内的猛硐老家居住。解放后的猛硐,一派新气象。项朝宗及其所部早已向人民政府投诚,走向新生活。
1956年,我再婚后,生有三男三女,儿孙满堂,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如今,老大老二盖起了砖房。我还担任了麻栗坡县政协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
岁月匆匆,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动乱年代,不知有多少千千万万个家庭像我一家那样遭受残破。有的甚至消亡。对比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新旧社会,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注:根据猛硐乡东瓜坪自然村李成才口述整理。
(作者:项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