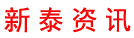>>>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1162个作品
文字:宣同珍
除封面图外,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原计划赴韩报到的中国留学生,近半数未按期入境,有人选择休学,有人选择在线听讲。与之相似的,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和企业职工,同样面临着延迟开学、延迟复工。对于聚居在北京五道口、望京地区的韩国人来说,眼前的中国与身后的故土都陷入非常时期,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增添了陌生新奇,也多了困扰与忧虑。
我们的实习编辑宣同珍,作为一个北京朝鲜族人,记录下身边数位在华韩国人的现状。一场疫情给他们带来的改变,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比预期得更为久远。
1
安静的五道口
一月中后旬,在黑龙江过春节的金秀爱,看到武汉发生严重疫情时,并没有特别紧张。直到她回到北京,发现北京比平日倍显空闲安静,才有切身的体会。
金秀爱是一个在华韩国留学生。与大部分留学生家庭不一样的是,她妈妈是朝鲜族人,爸爸才是韩国人。中韩建交后,父母相识恋爱,婚后生下了秀爱。由于母亲的籍贯在黑龙江,她这次去黑龙江,主要是为了看望姥姥和姥爷。
在韩国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感染时,她的韩国朋友几乎都回国了。回北京后,秀爱受其中一位朋友照顾家猫的委托,暂时住在五道口华清嘉园的一屋里。

上网课时,跳到桌子上的猫
往日,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五道口的酒吧和餐厅玩乐,特别是以韩国留学生居多。他们多爱抱团,会在酒吧门口前一起抽烟说笑,在灯红酒绿的照射下显得极度放松无谓,甚至到了凌晨两三点还有聒噪的打闹。如果没有疫情,现在的五道口会多些身着棒球衣骑电动车的韩国学生。
秀爱并不是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性格外向的她,也因不能出门和朋友见面而感到难受。“有些东西,是微信所无法替代的。”即便在家很难规划时间和集中精力,她也试着努力找回生活原有的节奏:每天照常做饭吃饭、给猫放粮倒水铲屎、查文献做综述、看些电影和做做运动。
对秀爱来讲,每个礼拜日都很重要。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疫情爆发后,教会不能再组织做礼拜了,为了安全,都改成家庭礼拜。独自在家的秀爱,会在网上找视频做礼拜,一般主日礼拜会有唱赞美诗、祷告、听牧师布道。和平时在教会做礼拜相比,秀爱少了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分享的氛围,但在她看来,“不变的是做礼拜即爱神,亲近神的一种方式”。
除了爱神,秀爱还得到许多韩国侨民团体的帮助,这些团体的正式名称为“北京韩国人会”。疫情爆发后,各省物资紧缺,为此,这些韩国团体会通过海外渠道,在望京、顺义、五道口等韩国人较多的地方发放口罩等物资,来帮助留在北京的韩国人渡过难关。
韩国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新天地”的宗教聚会,包括在网上流传一个视频,一位不戴口罩的牧师,眯着眼睛对信徒们说不要怕被病毒感染,最后还说一句“哈利路亚”。而这一句祈祷已变成微信里的表情包,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地传播。
“韩国国民应该对这些异端保持警惕。”同时,她也并不担心因为邪教的行为而使得周围人对其信仰造成误解。在她看来,投靠邪教者,多为对现实无力或不满而去逃避的人。
而说到现实,由于韩国人口老龄化严重,新冠病毒对众多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秀爱并没有太多在韩国生活的经历,只是每次回去,会发现“街上的老人越来越多,公交车司机也多是老年人”。
“只希望尽快过去吧,和朋友们再次见面。”她如是说。
2
疫情下的毕业季
2月10日,闵盛所读的大学封校了。面对这一次非同寻常的毕业季,他为留在中国就业感到格外焦虑。
闵盛四岁的时候,就随家人来到北京。他没有读什么国际学校和国际班,而是和许多中国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上课、考试,也很爱打篮球,直到上大学,才和很多韩国留学生有过接触。但早已“中国化”了的他,习惯上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读的是新闻学,比起读大量的书籍论文,他更擅长有实操性的摄影。读研期间,他常和导师一起组织外出,去中国各地乡下拍摄纪录片,内容多为邻里日常农作和来往、仪式活动等。早在研一的时候,他就打算做一部小纪录片,以作为毕业设计,内容以学校师生的日常为主。“弄成那种大纪录片是很难的,而且,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自己什么定位很重要。”
但疫情忽然砸晕了闵盛,让他感到每一天都不可预测。错过秋招的他,只能在这次更难的春招尽可能抓住机会;即便疫情当下,也不代表毕业设计、答辩等事宜会变得简单。再加上六月末签证就到期了,在此之前,他需要确定工作。
对这一切,“我真的太难了。”他总是重复这句流行语。“但其实现在大家都很难,不是吗。”
封校期间,除了去食堂吃饭,闵盛基本就在宿舍里。“片子剪得差不多的,最主要是看各大企业的招聘信息。”他还是院系篮球队的主力,但读研期间,身体肥胖了不少。借特殊时期的空闲时间,闵盛常去宿舍楼里的健身房锻炼身体,卧推、深蹲、跑步……运动能尽可能让他不太焦虑。有时,他也会去看先前在微博上保存下来的武汉摄影视频,“记录总是有意义的。”

宿舍楼里的健身房
宿舍每天都会有管理员来测学生体温,闵盛的体温总让人哭笑不得。额温枪到他头前,“嘀”一声后,管理员瞪着大眼睛,也不知道问人还是问机器,说:“怎么才31.3度?”有时候,闵盛的“体温”还会飙升到40多度。他会就此拿这件事在一些小群逗乐,群里的朋友回复大多是:你有毒。
本硕七年都在一个学校的他,太熟悉学校的一切。然而,“感觉跟做梦似的,不知道是因为要走了,还是因为疫情,又觉得很陌生”。
一次晚上,他想出宿舍在学校里走走。穿好衣服戴好口罩后,下楼接受管理老师的检查。老师看到这位“重点隔离对象”,拿起额温枪照着闵盛的脑袋。
“36.5度,怎么正常了?”
闵盛和管理老师一相视,笑了很久。
那是他近些天最开心的一次。
3
被改变的生活
京仁说:“疫情对我改变很大。”
和很多韩国孩子一样,京仁在韩国出生,三四岁时就来到中国了。先是在山东度过童年和青春期,山东韩国人虽多,但京仁基本是和本土孩子一起上课学习,大学则是在北京念中文系。按计划,他假期是要回韩国,但因疫情而作罢。
京仁对外界的看法很敏感。在山东上学时,隔几天就会听到如“韩国棒子”、“抄王之王”等歧视性的话。由于同学几乎都是本地人,他不敢说什么。“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称呼,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话不好。”渐渐地,他的性格有些孤僻起来。
但这样的经历没有使他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的自然反应是有距离感吧。”来北京上大学后,尽管有很多韩国留学生,但因为交往和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京仁没有选择强行抱团。即便念的是中文,他更喜欢阅读历史,包括从小听的歧视性词语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他都会逐一考究。那时候的他觉得自己有些幸运,因为性格的孤僻能让他不受太多干扰,去读些历史。
在开始知道武汉有人传人的病毒传播时,京仁并没有特别在意,在校外合租屋照常看历史书和纪录片。直到病毒传播相关信息真正疯狂起来,甚至到封城的地步以后,他才感到事情变得不对劲。
随着疫情逐渐严重,各种不好的消息时刻让京仁倍感痛苦和焦虑。他说:“这些消息就像在我的大脑里爆炸了一样”。他想试着看书来转移注意力,“根本就没用,看到密密麻麻的字心情就很乱。”京仁也经常性的失眠,即便是醒来也一直躺着,“很无力。”他还说,“我很少有这样的感觉。”
京仁自己也不清楚过了多少天,心情才缓解许多。

京仁出门散步时,常会眺望家旁的这条小河
一次出门买矿泉水,京仁看到四周排队等候的人群。他结完账后,抬头对收银员说:“谢谢,辛苦您。”“不客气。”收银员笑着回答道。
彼时的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所生活在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自己是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是在于他们很努力地生活。”
自此,京仁试着与社会建立联系,比如找一些可靠的渠道去捐一点钱,或者在小区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就稍微鞠个躬,社区人员也会稍作低头摆一下手,以示回敬。这些都会令京仁感到开心。
历史学者罗新的访谈推出后,京仁反复读了很多遍。京仁也渐渐能在关注疫情和读历史书之间有所平衡。他遵循罗新的话,去读《瘟疫与人》这样的书。京仁知道,疫情深刻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但这种痕迹,使得他“重新面对每一个人和生活”。
4
“是时候复工了”
56岁的朴胜宇,在中国生活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他在北方某一个县城的箱包工厂当部长。和往常一样,到春节假期,他就来北京和儿子一起过年。唯一不同的是,今年儿子总会多次打电话嘱咐他一定要戴口罩。
和许多人一样,朴胜宇被疫情的各种消息轰炸。1月23号来到北京后的翌日,就有报道称试剂盒供不应求,紧接着,就是武汉人在全国各地遭到歧视的消息,再接着发生病毒来源探究、一线医疗物资严重不足......尽管朴胜宇在中国生活多年,但早年多依赖朝鲜族同事的翻译,他的中文并不好。这些消息,有儿子和他分享探讨的,也有从韩国的网站上知晓的。几乎任何中国的消息一出来,第二天就能在韩网上看到。
朴胜宇所管理的箱包工厂规模并不大,除了向内地发货,也会往韩国、俄国出口。在家隔离期间,“有不少中国的客户,还有韩国的客户都跟我有电话联系,谁都希望尽快结束并复工,但不免也有直接取消订单的”。由于外国人身份,他所注册住宿登记的县城派出所,会给他打电话询问情况。“以前都会问我何时回来,现在只问我什么时候出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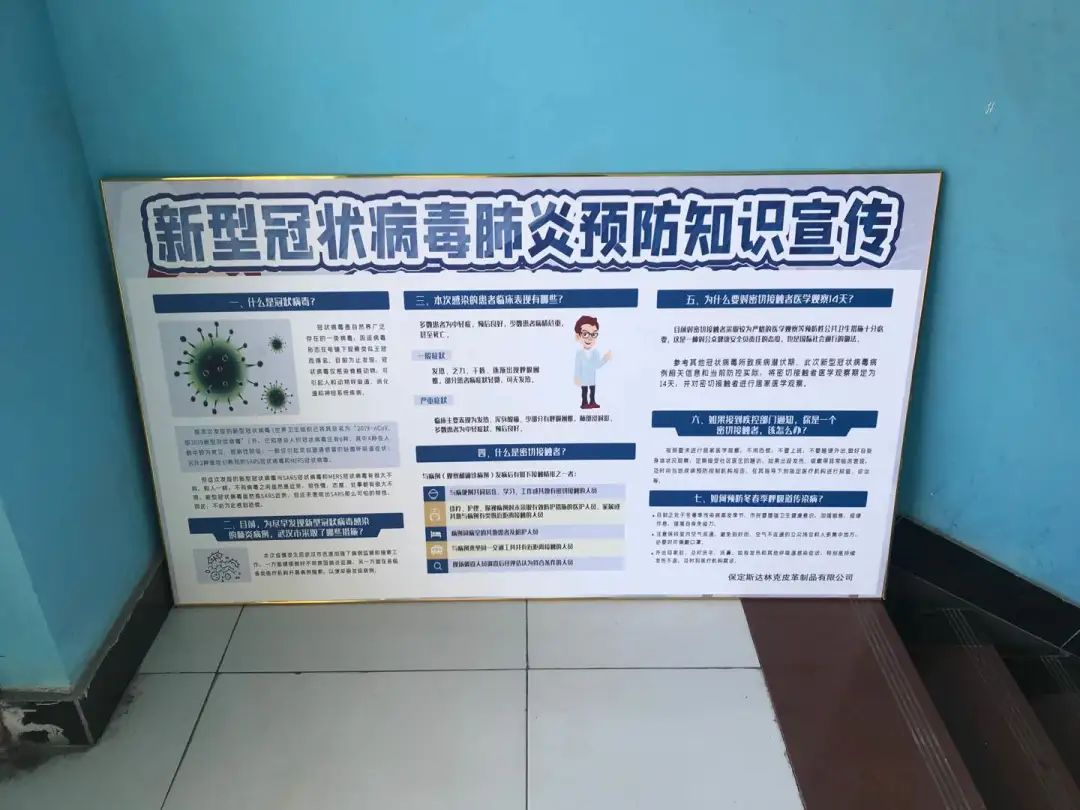
厂内楼道里,有关预防病毒的宣传板
朴胜宇自认为“这一生过得并不是那么成功”。大学学工商管理的他,在一次实习中偶然遇到一位商人,期间没有过多接触,“只是感觉他的眼光吧,不太一样。”九十年代初中韩建交后,那位商人来了趟北京,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前景以后,就回韩国拉上胜宇一起做生意。
“那时候已经有工作并结婚生子了,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了解,但是想试试看。”他和家人商量好、办好护照签证、填好各种表格后,就随那位商人来到中国。在北京顺利建立公司并有生意做后,他就说服家人一起来北京生活。朴胜宇的妻子原先对中国不免带有冷战时期的有色眼镜,但为了家庭完满还是带上孩子一起去了。
公司谈不上很大,但一直很稳定,朴胜宇也一直在努力赚钱养家,一家人的生活“很普通但也不错的”。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遭到严重打击,而那位带朴胜宇一起做生意的商人,没有说什么就拿公司剩余资产跑掉了。这场意外使得朴胜宇在家待业一个月,“没了工作,工作签证却还有效,挺可笑的吧。”
所幸在华期间,朴胜宇也结识不少韩国商人,其中一位年岁较高的韩国人愿意接纳他。见面谈话后没多久,他很快就加入到这位韩国商人的工厂管理队伍中去了,也就是现在的箱包工厂。后来这位韩国商人年岁愈来愈高,打算回国养老,让朴胜宇和一些元老一起接管工厂。
后来,大工厂有过两次搬迁,生意照做,但规模变小了很多。2017年4月,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开始运行,虽然不像十二年前的金融危机那般严重,但萨德事件也给予工厂不小的打击。“好多生意没了,做好准备发货的箱包全堆在厂中心的空地,很难处理”。最后,他只能硬着头皮向老朋友借钱渡过难关。直到去年年初,工厂才开始再次步入正轨,但债务没有还清。这些经验教训让他总结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与你有关系。”
在隔离生活期间,不同于其他人,朴胜宇没看《切尔诺贝利》《血疫》,看的多是诸如《宾虚》《日瓦戈医生》《出埃及记》《从海底出击》等他从小看到大的经典老电影。他不太想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要和当下联系,当然,除了一次:奉俊昊获奥斯卡奖后,他特地看了《寄生虫》。有不少评论认为内容过于夸张,但在朴胜宇看来,“电影里的穷人和富人的样子,跟我在韩国看到的,真的很像。”
朴胜宇和儿子也有互动,会一起聊历史、说笑解闷、戴口罩出门买菜。他也酷爱打台球,但疫情当下许多台球厅早已关门,于是就借用儿子的QQ号来打QQ桌球。儿子曾听母亲讲过,父亲台球水平极高,还在韩国的时候就经常夜不归宿。“儿子看我玩台球游戏,就问我:‘又赢了?’我就说:‘嗯,赢了。’”
而至于韩国国内反对派的反华游行,和就此针对文在寅的弹劾请愿,朴胜宇不无有些愤怒,“为了反对而反对,到底有什么意义,在疫情面前,就不能一起合作吗?”
日复一日,朴胜宇看到北京街上来回的车辆变得多起来,多半是复工的人。他倒没有了太多刚到北京时的苦恼和焦虑,他早已准备好开始返工,以结束这一不同寻常的长假。和同事商量好后,他就开始收拾东西。走之前,嘱咐儿子照顾好自己,儿子也对朴胜宇说千万要小心。“这中间没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是要该做些什么了。”
3月2号上午,工厂派车到北京来接朴胜宇回去。到工厂放下行李,在办公室和卧室收拾消毒以后,他长呼一口气,“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投稿邮箱:istory2016@163.com
长期征稿,稿酬1000-2000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