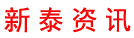"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
——张爱玲《造人》(一九四四年五月)
张御史的少爷,黄军门的小姐,十九岁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童玉女。
五年之后,一九二○年九月,母亲生下我姐姐,小名小煐。次年十二月,母亲生下我,小名小魁。此后十多年,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和父亲离婚后又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三八年她逃离我父亲的家。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听到父母的争吵,面对他们的恩怨分合。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其间的波折和伤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
与二伯父分家而治,搬到天津去。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一九二四年,姐姐四岁,我三岁。如果母亲没有在那一年出国去,姐姐和我的童年应该是富足而幸福的。
然而母亲和姑姑走了。我和姐姐常由保姆带着,在花园里唱歌,荡秋千,追逐大白鹅。
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
如果父亲能够本分守成,不花天酒地吸大烟,母亲也不会伤心出国,我们的生活是可以一直平顺而宽裕的。照我姐姐后来的分析,是说我父亲一直在二伯父治下,生活太拘谨了,一旦如愿地分家而治,就如野马脱缰,难以收心,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
我的大伯父早逝,二伯父大我父亲十七岁:他们是我的第一位祖母朱芷芗所生。第二位祖母边粹玉并无生育。第三位祖母(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生了我父亲及两位姑姑;但大姑姑早年在杭州病故。我祖父一九○三年去世时,二伯父二十四岁,我父亲才七岁,姑姑二岁。
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祖父去世后,表面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俭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华。三祖母一九一二年去世后,家里仍残留着封建习俗与家规。长兄如父,长嫂若母,我父母婚后与他们同住自然觉得很拘束;我母亲因而常常回娘家解闷。后来我看父亲那一时期的日记,差不多每篇都写着"莹归宁":莹大概是母亲的小名。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张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出任该职),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的分了家。一九二三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我母亲思想开明,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姐姐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更为深恶痛绝。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纳妾、吸大烟等等行径,往往是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因为家里并无她们发言的地位。我母亲对父亲的堕落则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
姐姐在《童言无忌》里说: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姐姐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所以我有记忆的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姐姐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有时也上公园走走,或到亲戚家玩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姐姐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姐姐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姐姐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姐姐一个,我也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
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母亲和姑姑走后,我父亲的生活更为堕落了。原来养在外面的姨太太,也干脆住进家里来。成天出出进进的,都是那姨奶奶的姐妹淘,莺声燕语,好不喧闹。
家里来了那些客人,姐姐的保姆"何干"和我的保姆"张干"就把我们带到院子里玩。姐姐很爱荡秋千,因为她比我勇敢。我在一旁看着,很羡慕,但不敢坐上去。姐姐还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但我一句也没学会。
姐姐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姐姐早慧,观察敏锐,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从而"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虽只比她小一岁,对这些事?一直是懵懂无知的,觉得保姆都差不多:无非是照顾我们起居生活,吃饱穿暖,陪我们玩耍,不让我们去打扰大人的生活。
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所以,她"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这句话,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姐姐在《私语》里描写的这段情景,如今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从小在姐姐心目中的分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地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姐姐描写的那般,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姐姐并未写出我们搬离天津的真相。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六年。一九二八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姐姐八岁,我七岁。
关于我们搬回上海的原因,姐姐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即使在她晚年写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里,也只有以下几句简单的描写:
"他一直催她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
"我们搬到上海去等我母亲、姑姑回国"。
"我八岁搬回上海,正赶上我伯父六十岁(编按:应为五十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虽然姐姐后来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我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没把他搬离天津的原因写出来。她在《私语》里也仅说是父亲的姨太太"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管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一九二七年一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一九二八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母亲坚持送我们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我母亲决定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挽救她的婚姻。既然我父亲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认为这个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她是个母亲,当然想念儿女,想回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姐姐和我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父母亲都没有正式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姐姐和我的教育,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我们三四岁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我们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说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后来也学英文和数学。

但我母亲去英国游学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她回国后,为了这个问题和父亲争吵多次,我父亲就是不答应。
办离婚手续时,母亲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姐姐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姐姐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姐姐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我姐姐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我的表哥黄德贻回忆说,我父母离婚完全是我母亲采取主动,我父亲根本不想离婚。但他当初要我母亲回国曾答应两个条件,"戒除鸦片"这个条件没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我表哥说,我母亲请的是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我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着我父亲那个样子,就问我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我母亲答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父亲听了这话后,才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听着父母吵架,起先是陌生的,渐渐我就害怕起来了。
我们刚从天津搬回上海时,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就暂住在武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所石库门房子里。过没多久,母亲和姑姑回来了,就搬到现在的陕西南路一处叫宝隆花园的一幢欧洲式洋房。屋顶是尖的,门前有个小花园,进了门有一个挂衣服搁雨伞的木橱,客厅很宽大,还有个壁炉。那洋房共有四层,顶楼作为贮物间。姐姐和我在楼梯间跑上跑下,起先很兴奋,因为母亲和姑姑回来了,家里热闹了许多。有时母亲请朋友来玩,就在客厅里弹钢琴、唱歌,姐姐和我坐在一旁看着,觉得很快乐,很幸福。有母亲在家,确实是不一样了。那时母亲三十二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我,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但是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和母亲又开始吵架了。关于这部分,我姐姐的记忆是:
"他们剧烈的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私语》
张干和何干陪着我们,轻声地说道:"又吵起来了!"
我们虽然仍逗着狗玩,但我心里很害怕。以前他们也一定吵过架,那时我还小,没留下记忆。住天津的时候,母亲出国去了,偶尔听到的是父亲呵斥姨奶奶的声音。回到上海来,听着父母的吵架,起先是陌生的,渐渐我就害怕起来了。
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觉,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
回复到天津时期:只有佣人和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不久我父亲又开始吸鸦片,我母亲闹着要离婚。闹了好久,我父亲终于同意了。从复合到离婚,前后不到两年。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那时姐姐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姐姐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姑姑送父亲住进中西疗养院戒除吗啡毒瘾。
离婚这件事,对我父亲的打击可能是很大的。抽鸦片已经不能麻木他的苦闷,进而开始打吗啡了。他雇用了一个男仆,专门替他装大烟和打吗啡针。他的身体和精神日趋衰弱,神经也开始有点儿不正常。亲戚朋友听说这个情况,都不敢上门来看他了。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有一天我父亲只穿了一件汗衫和短裤,仍然嫌热,就把一块冷毛巾覆盖在头上,两只脚浸在盛满冷水的脚盆里。那时正放暑假,姐姐在家。父亲看到我和姐姐,眼光呆滞,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家里的佣人看他那样子都很害怕,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我看了也很害怕,以为他快死了。
后来佣人就打电话给姑姑,把情形说给她听。姑姑来到我家,看见父亲那呆滞的、奄奄一息的样子,立即决定把他送到中西疗养院去住院治疗,戒除毒癖,挽救他的生命。
我姑姑是相信西医的。她请了中西医院里一位名叫Lambert的法国医生为我父亲主治。他当时采用的戒毒措施是替我父亲注射盐水针剂,借以恢渐冲洗体内的吗啡毒素。另外还用电疗按摩他的手足,促进血液循环,使手足的功能恢复正常。
这样大约治疗了三个月,我父亲才逐渐恢复健康,戒除了吗啡的毒瘾。不过鸦片他仍继续抽着。
朱老师捏着喉咙学女声朗读《海上花列传》。
父亲出院后不久,我们就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十号的一所小洋房里。我舅舅家也住在那条里弄里的明月新村,和我家只有几步之隔。父亲虽已和母亲离婚,和我舅舅的来往并未受影响。我舅舅也是靠吃遗产的遗少,舅舅、舅母也都吸鸦片。父亲把家搬到那里,一方面是可以常去找我舅舅一起吸大烟聊天,另一方面是舅舅家孩子多,姐姐和我也可常去找表姐、表哥玩。
那几年中,我记得姐姐一到寒假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精神非常专注,细心,不许我在旁边吵她。我知道她总是把自认最满意的圣诞卡拿去姑姑家,请姑姑代为寄给我母亲。
姐姐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姐姐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后来姐姐就不再去了。
那时我父亲延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老师,在家里教我念古书。朱老师性情温和,待人很亲切。姐姐如果在家,也常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姐姐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姐姐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口白朗读书中妓女说话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姐姐和我听了都大笑不止。姐姐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寒假里她自己编制了一份报纸副刊。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
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姐姐的创作才华。

姐姐小的时候,个性是很活泼的。记得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吃饭,我舅舅一家也都来了;他们家是女孩子多,另一位贵宾则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就叫"哈巴",长得很逗人,招人喜欢。姐姐和舅舅家的几个表姐,不知怎么商量的,在我们做游戏时突然把"哈巴"抢了去,关在楼上一个房间里。楼下的男孩子--"哈巴"的两个哥哥、我表哥与我——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我姐姐发号施令,指挥若定,我们这几个男孩子都不是她们的对手。后来因为要开饭了,娘子军才休兵,把可怜的"哈巴"放出来。
姐姐与舅舅家的表姐感情很好。放假回家就往她家跑,也常约她们一起去看电影、逛街。那时她也常去姑姑家。从姑姑那里可以知道母亲在国外的情形。母亲写信给她,也都是寄到姑姑家转的。
姐姐读高一那年,我才读小学五年级。
一九三四年,我姐姐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底,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利亚女中那么高级。圣校是美国教会学校,和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中西女中——同属姐妹校;学生全部住校,学费也很昂贵,校址在现在的中山公园以西穿过沪杭铁路不远的一座幽静的西式建筑里。不过解放之后,听说那里已改为工厂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五日,圣玛利亚和中西女中这两所贵族女中合并成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校址在中西女中旧址)。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父亲再婚前不知我后母也吸食鸦片。
一九三三年,房地产价格上涨,我父亲的经济情况好转,原来已不大来往的亲戚又开始走动。其中有三位姑表亲往来得尤为频繁。一位表姑父是交通银行某分行的经理,一位是一家外商银行的华买办,另一位是律师。他们三家几乎每天都有饭局或牌局,也几乎每次都邀我父亲去参加;后来就把我父亲介绍给日商住友银行的华买办孙景阳做助手,处理与英美银行和洋行业务的书信往来。父亲在津浦铁路局做过英文秘书,处理英文商业信函等事务还颇内行。外商银行的华买办,主要业务就是做投机、买卖股票、债券等等,我父亲也从那里学了一些实务。
因为与孙景阳朝夕相处办公,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应酬也越来越频繁。那位表姑父了解两家的情况,就提议把孙景阳父亲庶出的一个女儿介绍给我父亲,并亲自去做媒提亲。
孙家是个大家庭。孙景阳的父亲孙宝琦有一妻四妾,子女二十四人(八男十六女)。要介绍给我父亲的这位庶出的女儿叫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当时已三十六岁。据说她很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及对外应酬。和她哥哥、姐姐的婚嫁比起来,攀上我父亲这门亲,似乎有些低就。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难以和权贵子弟结亲。只是婚前我父亲并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
"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但还是发生了!
这门亲事很快就说定了。一九三四年夏天在礼查饭店(今上海大厦附近)订婚,半年后就在华安大楼(现在的金门酒家)结婚。
父亲再婚那天,姐姐和我都参加了。二伯父、二伯母、姑姑及舅舅一家也都来了。姐姐和姑姑、表姐她们坐一起。我和表哥、堂哥、堂弟等人坐一起。那年姐姐十四岁,读高一,我十三岁,读小学五年级,都是最敏感的年龄。看着婚礼的进行,我想着远在欧洲的母亲,不知她那时在哪一个国家?生活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可能再婚?我也想到这位后母不知是个怎样的人?我们一家以后要过着怎样的生活?姐姐从来没和我谈过父亲再婚的事,大概认为谈不谈都一样吧?

许多年后,我才从《私语》里看到她对父亲再婚的感受是那样的激烈: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后母怂恿我父亲搬进有二十多个房间的大别墅。
后母进门后,我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她确实想表现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的手腕,不但抓紧日常生活开支,对佣人的工作也加以调整。我父亲用的一些男仆和母亲原来用的几个女仆都被辞退了,把孙家原有的男女仆人补了一些进来。
对于住的方面,后母也有意见。她认为现住的康乐村十号洋房太狭小,劝我父亲搬家。正好我二伯父名下的别墅有一家房客搬走,房子空了出来。那别墅是李鸿章给我祖母的陪嫁。祖母在世时,二伯父一家、我姑姑及我父亲都住在那里。姐姐和我,也是在那座大别墅出生的。祖母去世后分遗产,别墅落在二伯父的名下。我父母搬去天津后,二伯父嫌它大,自己不住,一直都在出租。
那别墅位在现在泰兴路(当时叫麦德赫司脱路)和泰安路(当时叫麦根路)的转角上,隔着一条马路就是苏州河:过河就是闸北区。它是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方建筑,房间多而进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有二十多个房间。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物,算是个贮物间。
这样的房子,本来应该是大家庭住的,我家只有四个人(佣人不算),住起来是嫌太大了。但我后母看过后,也不管房租有多贵,一直怂恿我父亲搬进去。据我后来的猜想,我后母急于搬家,大概是觉得和我舅舅家离得太近了,对她不方便。
成长期结束了,但创伤还在成长。
搬进这样的大房子,布置家具等等,当然花了一大笔钱。那年我父亲还在银行做事,就快过四十岁生日了,后母当然极力张罗,务必风光气派,让我父亲有面子,也让亲友觉得她确实很会治理家务。至于花掉多少钱,她是不去算计的。我姐姐中学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所又老又大的房子里度过的。

一九三七年秋,她和后母吵架,被我父亲关在这房子的楼下。半年之后,她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
作者:张子静(1921-1997),张爱玲之弟。

原标题:《张子静笔下的姐姐:我的姐姐张爱玲(1)》
阅读原文